诗家总爱西昆好,今喜有人作郑笺
——刘学锴教授访谈录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谢琰
( 载《文艺研究》2018年第1期)
刘学锴,1933年生,浙江松阳人。1952—1963年,就读、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顾问。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李商隐研究及唐诗研究,擅长文献整理、史实考论、诗学阐释。主要著作有《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温庭筠全集校注》,分别荣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一等奖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安徽省2001—2003年社科成果奖著作一等奖及省图书奖一等奖、安徽省2007—2008年社科成果奖著作一等奖。此外,还撰有《李商隐诗歌接受史》《李商隐诗歌研究》《李商隐诗选》《李商隐》《汇评本李商隐诗》《李商隐资料汇编》《王安石文选译》《温庭筠传论》《温庭筠诗词选》《唐诗选注评鉴》等多种著述(含合著)。本刊特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谢琰博士采访刘学锴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缘结义山,心系京皖
谢琰 刘先生,您好!我受《文艺研究》杂志委托,对您做一次专访,想请您谈谈治学经验。非常感谢您能答应我们的请求。我首先想问,您是如何走上李商隐研究道路的?
刘学锴 我在高校工作将近半个世纪,但说来惭愧,研究领域太窄。1975—2004年整整三十年,除了给本科生讲课、指导研究生之外,我集中研究的领域就是李商隐,总共写了十来部有关李商隐的书、三十来篇论文。这里面,我认为稍微重要一点的,希望能为学界用上三十年的,也就是三部书:《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大家可能会奇怪,一个人怎么能在这么狭小的领域里孜孜不倦地劳作三十年呢?这一点,当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现在想来,当然有诸多主、客观原因。我们这一辈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时,多数同学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才来的,极少有人从小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我只在1952—1957这五年内,比较认真、系统地学了一些知识,浏览了一些重要作家的诗文集。但在1957—1976二十年里,能坐下读书研究的时间少得可怜。等到“文革”结束,想重操旧业,已经明显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尽量压缩范围,不把摊子铺大。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和余恕诚合撰《李商隐诗选》,1977年中华书局又约我们写一本小册子《李商隐》,我的李商隐研究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我戏称这种研究选择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压缩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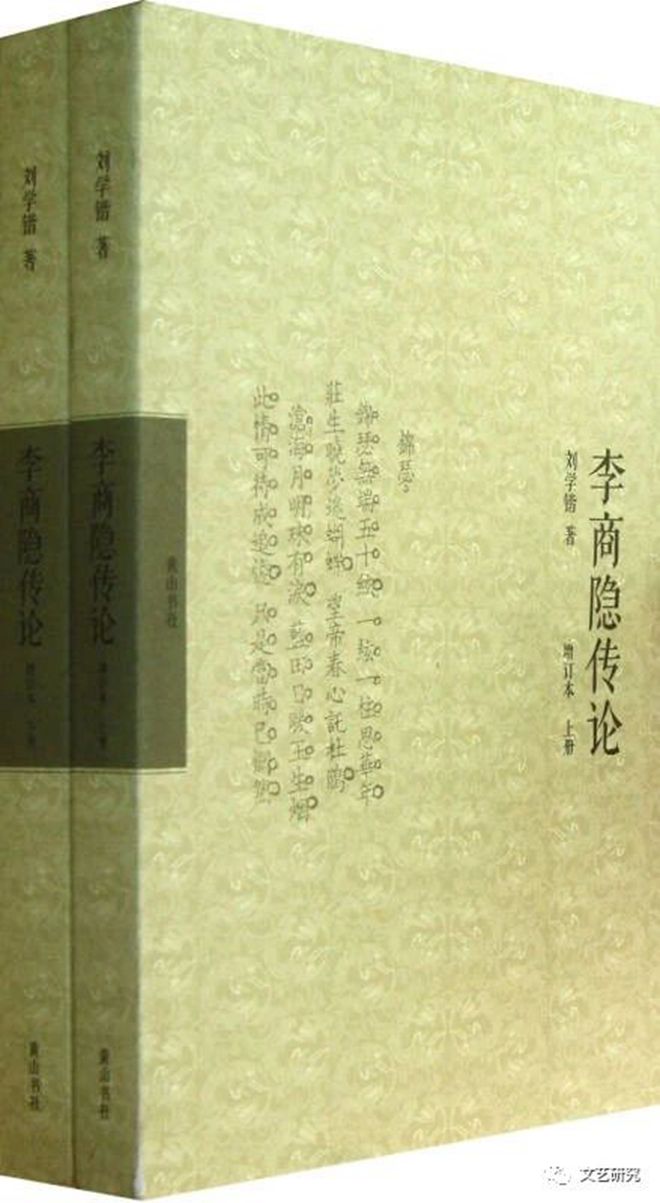
谢琰 我读您的书,感觉您不仅是从严谨的学术层面解读李商隐,而且是从情感、性情上去揣摩他。您觉得自己的性情、个性是否与李商隐有相通之处呢?
刘学锴 有一些吧。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这个因素可能让我小时候比较内向,有点感伤气质。我比较喜欢感伤类的作品。比如《诗经》里的《东山》《蒹葭》《采薇》,还有《古诗十九首》。我有一篇文章叫《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我发现李商隐总提到宋玉,所以写了这篇文章。从性情、个性来讲,我略带感伤气质,所以对感伤情调浓重的义山诗,有一种天然的契合与共鸣。
谢琰 除了主观原因,您与李商隐的结缘是否还有时代原因?
刘学锴 当然有,这是根本原因。在20世纪50—70年代,学界对李商隐是比较歧视和冷淡的,有时还把他当作贬抑的对象和批评的靶子,比如说他唯美主义、反现实主义。尽管李商隐也写过不少学杜甫的感时伤世、忧念国运之作,但他诗风的突出特征还是感伤情调、朦胧诗境、象征色彩,抒写内心幽隐情绪,歌咏悲剧性爱情体验、人生感慨。这些内容、风格特征,都和当时那种非常直接的“古为今用”的要求有距离,甚至相矛盾。而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古代文学领域掀起“李商隐热”,毫无疑问是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变化的自然要求和结果。1999年出版的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作家地位升降方面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李商隐过去只在讲晚唐诗歌时设一小节,而在这部书里却独立为专章,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公认的第一流大作家并列。这说明,对于李商隐这种类型的作家的思想艺术成就和价值的认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需要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文化环境。李商隐研究热的兴起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延续,有它的时代必然性。所以我在这三十年里集中研究李商隐,不妨说是时代潮流的推动。如果我没有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肯定会有别的学人来做,而且会做得更好。
谢琰 学术方向的选择,既要顺应时代潮流,也要符合学者的人生境遇和个性特点。但是,好的选择只是成功的一小步。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学术功底极为重要。您在北大求学和任教期间遇见了哪些先生?他们对于您学术功底的养成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刘学锴 学术功底很难说啦!我自知短板很多。当时北大的先生们,都特别强调系统读书。我从大二到大四,一直担任文学史课程的课代表,当时的授课老师是游国恩、林庚、浦江清、吴组缃四位先生。在同学中,我读的集部书确实比较多,但是经、子、史三部读得比较少。对于先秦典籍,我有点畏难。本科毕业时,游国恩先生可能有意留我做他的助教,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唐代,征得林庚先生的同意,做了他的第一届副博士研究生。除各段研究生都必须通读从《诗经》到《红楼梦》二十五部书外,林先生还要求我认真阅读自魏晋至五代的名家别集,认真撰写札记,定时送交。他会审阅批改,再让我到家面谈,指出优缺点,从观点到对诗句的理解都一一指出。这种严格要求和训练,使我受益匪浅。读研期间,林先生还让我做过一些助手性质的工作。他撰写《盛唐气象》的论文时,让我统计初、盛、中、晚唐四期诗人和各种体裁作品的数量,使我对全部唐诗作了一次通览。此外,当时受高教部委托,由林先生撰写新编《中国文学史》的隋唐五代部分。每撰一章,先生都要我先读这一章中涉及的作家诗集,并从中选出一部分代表性的作品。每章内容由他口授,我作记录,并整理成初稿。由于时代原因,这部文学史的撰写不久就无疾而终,但这段短暂的师生合作却长久保留在先生记忆中。1988年,沈天佑学友陪吴组缃先生来安徽师大参加《红楼梦》研讨会,还特意提及林先生在教研室会议上深情回忆起当年和我隔桌相对而坐、边口授边笔录的情景。我自己,当然更对这段合作经历难以忘怀。1959年北大中文系新建古典文献专业,将我提前分配到新专业任教,我师从林先生读研的经历就此正式结束。
当时古典文献专业的基础课,多由别的系的老师来上,比如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是由哲学系、历史系的教师来讲的,真正本专业的课,如古籍整理概论等,并没有开出来。当时吴小如先生从文学史教研室借调到文献专业,讲古文选读课,我和侯忠义担任辅导。小如先生指导我阅读《书目答问补正》《四库提要》,使我对古籍的总貌,特别是重要的经、史、子著作及其注疏有了大致的了解。他还让我仿照《四库提要》体例,为古文选读课选篇所从出的古籍用浅近的文言写提要。后来我参加《古籍整理概论》教材的编写,并开了“校勘学”这门新课,都与小如先生从目录学入手的指导分不开。我讲校勘学,一点基础也没有,都是自己找清儒和近人有关校勘学的专著和古籍校注著述来看,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才开出这门课。我和古籍整理结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与李商隐结缘,还和陈贻焮先生有关系。他是林庚先生转入北大后的大弟子。林先生主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时,他担任助教,我常向他求教。他给我们主持过很多次课堂讨论。在我印象中,陶渊明的课堂讨论非常激烈,陈先生的总结也特别精彩。我后来从事李商隐研究,首先得益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的几篇有关李商隐的论文。1992年他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命我担任第三分册的组、编工作,我责无旁贷。尽管我们私下里亲昵地称他为大师兄,但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师长。
谢琰 您在20世纪60年代调到合肥师院中文系,从那以后一直任教于此。安徽师大有一些旧学根底深厚的老先生,如张涤华、宛敏灏、祖保泉等,您和他们是否有过交流?
刘学锴 当然有啦。我刚进合肥师院,系里给我分的课是大学四年级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张涤华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也亲自出马和另几位老先生各上一个大班的课,集体备课时还常问我对某篇文章有哪些看法。说起张先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1963年7月底,我到系里报到,第一次见张先生,他就询问我在北大的师承,开过什么课。我如实说了。他听说我教过校勘学,好像有些吃惊。我当时不到三十岁,可能在他的意识里,这门课年轻人是不可能开的。他让我把讲稿给他看看。我实话实说:离开北大的时候,校勘学课由陈铁民和孙钦善这两位刚毕业的研究生来上,我就把全部讲稿留给他们了。这就是我和张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张先生当天回去在日记里写道:“刘君学锴,年不足四十,学有根底,甚可喜也。”他说我“学有根底”,可能就是因为我开过校勘学课吧。宛老当时是副教务长,还给艺术系开“词的格律”这门课,我听他的课,并给学生作辅导。1978年我们有硕士点的时候,宛老是带头人,具体工作就由我和余恕诚来做。宛老是词学大家,我在这方面没下过工夫,但对他的《二晏及其词》和一系列词学论文都曾拜读过。祖老一直担任系行政领导,交流机会更多,而且他曾在“安徽古籍丛书”编委会中担任职务,安师大成立古籍研究所,他也是带头人,我一直都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的著作我也都拜读过。三位先生都是行政领导兼学者,又都十分重才,在当时非常难得。

二、西昆解人,飞卿知己
谢琰 您的李商隐研究呈现出丰富、全面的体系。有诗集整理、文集整理、资料汇编、传记、接受史、选集选注、普及读物,还有很多专题论文。我想请您简单梳理一下这些成果是如何一步步编著出来的?
刘学锴 学术研究总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清代以前,李商隐研究基本未成气候。但从清代到民国,却出现了长期的李商隐研究热,可以列出释道源、钱龙惕、吴乔、朱鹤龄、徐树谷、徐炯、徐德泓、陆鸣皋、陆昆曾、姚培谦、程梦星、纪昀、屈复、何焯、冯浩、姜炳璋、钱振伦、张采田、苏雪林、岑仲勉等一长串研究者名单。岑仲勉先生说:“唐集韩、柳、杜之外,后世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隐。”我的李商隐研究,就是在如此丰厚的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起步的。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商隐诗选》,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商隐》,主要凭藉的就是朱鹤龄、冯浩的注本,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张采田的《会笺》,岑仲勉的《平质》,以及解放后报刊上发表的十来篇有关论文。这两本书,除了诗本身的疏解,在生平考证、诗文系年等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发现。但是在撰写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两个比较清晰的想法:一是义山诗旧注这么多,各家观点分歧很大,各有各的道理,很难定于一是,应该做一部“集解”式的整理本,对前人已有的考证、疏解、评点成果作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二是强烈地感到,这样一位“后世治之最勤”的作家,其生平行踪的考证、作品的系年、诗意的解说疏证乃至总体的评价等方面,都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纠正、补证,甚至彻底重新思考。特别是索隐猜谜、穿凿附会的解诗方法,从吴乔发端,到程梦星、冯浩大加发展,到张采田则登峰造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不走出索隐阴影,李商隐研究就会越来越陷入误区,不能自拔,甚至走火入魔。另外,冯浩等人在生平、行踪考证方面既取得了卓著成绩,也有重大失误和一系列缺失,由此导致对一大批作品的意蕴阐释发生偏差。今天再作义山诗的集解,应该尽量汲取前人这方面的教训,避免重犯类似错误。
谢琰 前人的具体观点分歧很大,方法层面又走入误区,所以既需要清理,又需要重塑。
刘学锴 对,就是在这两个想法的推动下,我从1976年10月开始继续收集资料,1979年4月正式开始撰写,至1983年竣稿,完成了一部一百五十万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这部书在汇校、汇注、汇评、汇笺的基础上,每首诗都附有自己或长或短的按语,对作诗背景、系年、内容意蕴、诗境诗艺进行考证、疏解。由于下了一番笨工夫,在各方面都有不少新的发现和结论。有了《集解》这个基础,1985年我又对《李商隐诗选》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修订,增选诗作近七十首,评、注结合,诗后的解说也作了比较彻底的改动增补,侧重诗艺,并改写了前言。这本书1986年再版,相比于1978年初版,已经判若两书。
此后一段时间,我有计划地写了一批有关义山诗的理论研究和考证文章,结集为《李商隐诗歌研究》,1998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前1993年,与余恕诚合作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卷》完稿交给中华书局,但迟至2001年方才出版。
从1995年开始,由恕诚提议,我又用全力对存世的三百五十二篇李商隐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校注。李商隐是骈文大家,他的骈文本身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而且与他的诗歌创作有密切联系与相互影响,既有以骈文为诗的一面,又有以诗为骈文的一面。而要想真正做好做细对李商隐生平的考证、诗文的系年考证,也必须熟读他的文章。他的骈文虽然不像诗那样有纷纭的解释,但典故特别多。尽管有徐、冯、钱三家的旧注、旧笺和岑仲勉《平质》作为基础,但需要进一步考辨、增补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我1995—1999年间,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全书的撰写。旧注是按体编排的,我改为按写作年月编排,又增补了七千多条注释和按语。在撰写过程中,发现了李商隐生平及诗文系年考证、诗文错简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陆续写成多篇考辨文章,分别发表在《文学遗产》《文史》《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古籍研究》《林庚先生95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总共一百三十四万字,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至此,“李氏三书”(诗集解、文校注、资料汇编)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我又根据1988年以来的新研究成果,对《李商隐诗歌集解》进行了全面的增补修订,增加了十四万字,于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增订重排本。有关李商隐研究的三项基础建设工程总算完成了。
这三部书完成之后,我觉得应该将我二十多年整理、考订、研究李商隐生平及诗文的成果,作个总结。于是又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撰写《李商隐传论》。由于有前面的几部书和几十篇论文作基础,再加上有五六十篇义山诗文鉴赏文章打底,这部六十七万字的论著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并于2002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又新增五章,改由黄山书社出版增订本。《传论》写成后,我又用了近两年时间写出一部三十六万字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对历代李商隐诗的接受历程、阐释史、影响史作了具体的梳理论述,2004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后,我的三十年李商隐研究历程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总的来看,我是沿着一条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由文献考证到理论研究的路线,滚雪球式地逐步推进的。我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传统方法,没有多少新花样,但自感每一步都走得比较踏实。

谢琰 您的李商隐研究之路,表面看来水到渠成,但其实暗藏着多少艰苦的思索和无穷无尽的枯燥的努力。您在李商隐生平考证和诗文系年方面有很多突破性的新发现,可以谈谈考证心得吗?
刘学锴 我先说一点总的想法。我觉得,如果真正想研究一个作家,最原始也可能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不怕麻烦,全面搜集前人、今人已有的校注、笺评、考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将该作家的全部作品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细读,并重新校勘、注释、疏解一遍,将前人、今人所作的全部传记资料、年谱,从头到尾认真审查一遍。真正下了这个笨工夫,相信一定会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新的结论。整个李商隐研究史其实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唐末到明末,为什么李商隐研究一直进展缓慢、不成气候呢?为什么清初朱鹤龄的诗文笺注本出来之后,李商隐研究就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热潮?这里面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时代原因,但是,从唐末到明末,一直没有学者下工夫做一部李商隐诗文全集笺注本,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没有这样的基础建设工程,研究的深度、广度、坚实厚重度,是很不一样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的考证新结论,都是从反复阅读中来,从校注、笺解、考证的过程中来。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一般性的阅读和亲自校注、笺解、考证的阅读,很不一样。必须要一字一句去抠。一般的阅读很容易滑过去的地方,有时会成为解决重大考证问题的关键。
谢琰 您对“江乡之游”说的辨正,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吧。冯浩、张采田二人主张,李商隐在开成五年九月到会昌元年正月之间,曾有“江乡之游”。此说在学界影响很大,几乎成为定论。您是如何考辨清楚的呢?
刘学锴 岑仲勉先生首先指出,这段时间内,义山正忙于移家、调官、作贺表,根本不可能分身作江乡之游。但很多学者仍然相信冯、张之说,因为他们有两条“铁证”:一条是义山有一首七律《赠刘司户蕡》,冯、张认为是刘蕡于会昌元年正月被贬柳州途中,与义山在湘阴黄陵晤别,义山作此诗相赠,所以证明会昌元年正月义山正在江乡。另一条“铁证”,是天复三年罗衮《请褒赠刘蕡疏》,冯、张引用其中文字:“身死异土,六十余年。”从天复三年上推六十余年,正好是会昌二年,也就是他们所推断的刘蕡的卒年。刘蕡在这一年卒于江乡。但是,我仔细阅读后发现,这两条“铁证”都不可靠。第一,《赠刘司户蕡》这首诗,不是作于刘蕡贬柳州的途中,而是作于他从柳州放还北归的路上。我是从哪句发现问题的呢?就是“更惊骚客后归魂”。“骚客”指遭贬的刘蕡。如果作于贬柳州的途中,如何会说他“后归”呢?“后归”,说明他此时已经离开柳州北归,只不过迟归而已。新发现的刘蕡次子刘珵的墓志说,刘蕡“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证实了我的推断:大中二年春初,李商隐奉使江陵返回桂林,而刘蕡正要奔赴澧州,两人在洞庭湘阴黄陵相遇,又匆匆作别。第二,冯氏所引“身死异土,六十余年”,并不是罗衮疏的原文。原文是这样的:“刘蕡当大和年对直言策,是时宦官方炽,朝政已侵,人谁敢言……遂遭退黜,实负冤欺。其后竟陷侵诬,终罹谴逐。沉沦绝世,六十余年。”“沉沦”,是指遭贬而沉埋不遇,“绝世”才指辞世。这两句是说,刘蕡自从遭遇贬谪沉埋,直至去世,至今已经六十余年了。“六十余年”,应该从会昌元年遭贬算起。这样,冯、张的“铁证”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整个考证过程还会涉及很多问题,但对于两个关键性“铁证”的驳正,就是从“后归”“沉沦”四个字的含义上作出突破的。我想,当代科技固然很发达,提供了很多便捷,有些考证会因此获得较快的成功,但我坚信,电脑无法代替人脑。像上面的考证,不但电脑解决不了,甚至连能否发现问题都要打一个大问号。
谢琰 您解决了一桩历史悬案。而且,“江乡之游”的有无,会牵扯到几十首诗的系年和理解。
刘学锴 你说得对。我的其他几篇考证文章,也都与阅读、注疏、系年中遇到的问题有关,而问题的解决也大都与关键性文字、诗句的正确理解有关。我还想申明一点,就是我的新发现和前人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比如以《李商隐传论》为例。从义山生平、行踪的总体轮廓来看,我所撰写的传,似乎与冯、张的谱、笺大体相同,差别不大。这也正说明了他们在义山生平考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加上岑仲勉先生的大量辨正,才使义山一生的经历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但如果将我撰写的传,与冯、张之谱、笺对读,便不难发现,无论是生平的许多重要节点,还是诗文系年、考证及对其意蕴的笺释,都有很多不同的结论和不少新的发现。另外,我叙述义山的每一段经历,都结合诗、文创作,尽可能细化、丰富化、切实化,所以我的义山传的许多具体内容,就与冯谱、张笺有很大不同。后人的考证、笺释,总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没有冯、张、岑所做的工作,我今天做起来会困难许多。后人的条件总体上较前人更好,理应将工作做得更细密、更精准一些。
具体的新考证结论,我作过粗略的梳理统计,大约有六七十项,涉及李商隐生平行踪、作品系年、诗文错简、版本系统等方面。关于诗文错简(主要是从《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一文引申出来)和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我都有专文考论,这里就不多说。我主要谈谈与生平、作品相关的考证。先以李商隐生年考证为例吧。过去主要有冯浩的元和八年生说、钱振伦的元和六年生说、张采田的元和七年生说。冯、钱各有所据,是因为李商隐在不同的文章中有关的记载本身有矛盾。张氏折衷冯、钱二说,但所作的解释不可信。我以为唯一的出路,是在承认双方所据材料都无误的前提下,参酌其他有关证据,作出推断。我的推断是李商隐生于元和七年初,而裴氏姊卒于元和七年末。这样就既与裴氏姊卒时李商隐“初解扶床”的叙述相合,又与会昌二年李商隐重入秘省时距裴氏姊之卒“三十一年”之记载契合,而开成二年正月所作《上崔华州书》“愚生二十五年”之语也可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特别是李商隐《梓州道兴观碑铭并序》中提及自己大中五年赴梓幕时正值“陆平原壮室(应为强仕)之年”,即四十岁,从这一年逆推四十年,正生于元和七年。这条证据,冯氏未见,而钱、张忽略。此外,我发现同年初秋《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一诗也暗用陆机《叹逝赋序》之典,也可证明商隐大中五年确为四十岁。再说句题外话,李商隐那么善于用典,却把常用典“强仕”错成了“壮室”,这很有意思。
谢琰 考证真是一项系统化的工作。您对李商隐各类作品都极为熟悉,综合排比,才能得出最无窒碍的结论。您常能从一句诗文乃至一个语汇的读解中,发现前人的错误和新的线索。反过来,您的很多考证结论,又可以帮助读者重新理解诗文语句。解诗和考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刘学锴 是的。比如诗文系年,会直接影响诗意的把握。像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很多注家都认为是寄内诗。但我发现,除了姜道生刊本《唐三家集》作“寄内”,其他旧本皆作“寄北”。而诗中的“巴山”,是义山在梓幕期间的诗文常用语,指梓州一带的山。而此时,其妻王氏已卒二年,何来“寄内”呢?其实不仅是系年了,其他有关名物、典故、人物的考证,也往往和理解诗意密切相关。比如《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诗中的“巴西”,其实指的是唐朝绵州巴西郡之巴西县,不是汉代的巴西西充,后者在唐代称果州。旧注误解“巴西”,于是有种种穿凿附会的解释。如张采田牵扯到义山至东川访杜悰,这纯属子虚乌有。再如《别智玄法师》诗,智玄即知玄,《高僧传》里有记载,和义山有交往。因为诗的首句是“云鬓无端怨别离”,所以冯、张都以为这位不是高僧,而是女道士。其实,“云鬓”是指自己妻子,首二句说自己十多年来到处漂泊,屡次更改归隐山林的日期,与妻子长期别离,以至云鬓佳人怨别。所以整首诗是别知玄时自我抒情,和女道士毫无关系。当然,穿凿附会的风气,批判起来容易,但真正自己做起来,也很难避免。比如义山名作《杜工部蜀中离席》,实际上学习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写法,仿效杜工部体,悬拟杜甫当年在蜀中离席上的所见所感,并不是在写自己蜀中离席的情感。程梦星、冯浩都不明白这一点,而是作出各种猜测,附会时事。《李商隐诗歌集解》初版中,我引大中六年四月党项复扰边之事以解读颔联和腹联,也是误解了。到2004年增订重排时,才改正过来。
谢琰 听您举例子,我愈发感到解诗之难。我读《集解》,觉得受益最多的是每首诗集注、集评后面所附的按语。我相信很多读者都有同感。后来读您的专题论文,会觉得其中的某些重要想法、灵感,在《集解》中都有闪现。您可以谈谈这方面的写作心得吗?因为现在有些研究者的选题是本末倒置了。他们先有观念或方法,再去找材料证明或找例子演示。
刘学锴 你说得对。我在对一首一首作品进行笺解的过程中,有时会触动对某些问题的想法,然后再写成文。我有个体会:文学作品不能硬作,论文也不能硬作。如果没有对具体作品特别是代表性作品的感悟和理解,要想提炼出有意义的题目,恐怕很难。即使作起来,恐怕也不会有切实的发现。我自知短板很多。比如对佛、道二教,我基本不懂。我的理论思维也比较差。我真正感到下了切实工夫、有点自信的研究,还是考证方面。关于理论研究,如果一定要说心得,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在选题方面,注意选取一些前人、今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而又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李商隐和宋玉的承传关系以及感伤主义文学传统、义山诗与词体的关系、义山诗抒写人生感慨的特点、玉溪诗与樊南文的关系、义山的白描诗境等等。别人探讨玉溪诗与樊南文,多注意其以骈文为诗的一面,我则侧重于谈樊南文的诗情诗境。别人多关注义山诗的沉博绝丽、用典对仗的精工等,而我对义山全部诗作了统计分类,发现白描是其创作手法与诗境的重要特征,且反映了义山本色,所以撰文专论。二是一些属于诗歌本体研究的论题,如咏史诗、咏物诗、无题诗、政治诗、七律、七绝,前人、今人多有论述。对于这些论题,我迎难而上,力求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主要是结合这些题材、体裁历史的发展来谈义山的特点和贡献。这些讨论,我觉得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李商隐、恰当评价其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李商隐作为文学史上的大家,一定要用史的意识、发展的意识来研究他。无题诗属于自创新体,当然要研究,但作为一个大家,光有无题诗是不够的。他必须在一系列传统题材、体裁中都有一流之作和创造性贡献才行。三是我比较重视义山的个性,包括生活个性、思想性格、悲剧心态和艺术个性。比如我讨论他的咏物诗,明确提出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发展这一内容上的突出特征。还有,对他的诗的比兴象征和朦胧意境,人们注意较多,但我比较强调他的诗的那种有意无意之间的寄托,包括许多名作,如《乐游原》《嫦娥》以及一部分无题诗。其诗歌意蕴的虚泛、多重,均与此分不开。四是在研究方法上极力避免穿凿比附、索隐猜谜,主张融通。义山诗歧解纷纭,其中固然有走火入魔者,但也有很多人是从不同侧面感受、阐释义山诗的丰富内涵,从而得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不必扬此抑彼、排斥异说,而应该在把握其特点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融通众说。我对《乐游原》《嫦娥》《重过圣女祠》《锦瑟》以及一部分无题诗的解释,都力求融通众说。这会使诗歌阐释更富包容性、开放性,而不是追求定于一尊。
谢琰 进入21世纪后,您开始从事另一项新课题,就是温庭筠研究。从目前成果来看,这就像是李商隐研究的缩小版,但仍然自具体系。您先后推出了《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传论》《温庭筠诗词选》三部著述。您觉得,研究温庭筠和研究李商隐有什么不同?
刘学锴 我的温庭筠研究,未成气候。原因有二:第一,我下的工夫比起三十年治李义山,远远不够。第二,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现存的文献资料所能提供的新发现的可能性很有限,很难得出比较多的崭新的考证结论。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注本仅曾益原注、顾予咸和顾嗣立补订的《温飞卿诗集笺注》一种,疏漏很多,与义山诗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注本根本无法相比,尤其缺乏像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那种精益求精的著作。他的生平考证也非常疏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陈尚君、施蛰存的文章发表以前,连他的生卒年也未弄清,其他生平经历中的疑点与空白点更多。他的词,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温词的单独注本也到近年才出现。赋与骈文则一直没有人作过校注。我在温庭筠出生居住地、诗文系年、晚年生平事迹考证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其骈文也第一次全部作了注,当然还有不少疏漏,有待后贤匡正。

谢琰 高质量的作家研究会改变文学史的写作。根据您的研究,有可能抬升温庭筠的文学史地位吗?或者说,应该如何评价他的文学史地位?
刘学锴 文学史里写温庭筠,通常将诗、词安排在不同章节论述,骈文偶或一提,小说则缺位。学者研究温庭筠,也都是对各种体裁进行分割研究,这样就很难形成完整的印象。很多人只把他当作大词人来看待。现在,我把他的诗、词、文、小说合编成一部《温庭筠全集校注》,可能会有助于学界更综合、全面地去看待温庭筠,也许会提高他的文学史地位吧。温庭筠的诗,在晚唐不如小李杜,但显然超过许浑。现在管琴等学人写文章专论陆游七律的“熟”,其实这个倾向从许浑就开始有了。所以,在晚唐诗四大家里,温庭筠应该排第三。再加上他的词、骈文、小说的创作,他的地位应该比现在文学史评定的更高。比如他的小说,用现代眼光来看,能称为小说的不算多,但有些确实写得不错。像《陈义郎》《窦乂》《华州参军》,置于唐代一流小说里也不逊色。尤其是《窦乂》,塑造了正面的、成功的商人形象,意识很超前,写实的笔法也很高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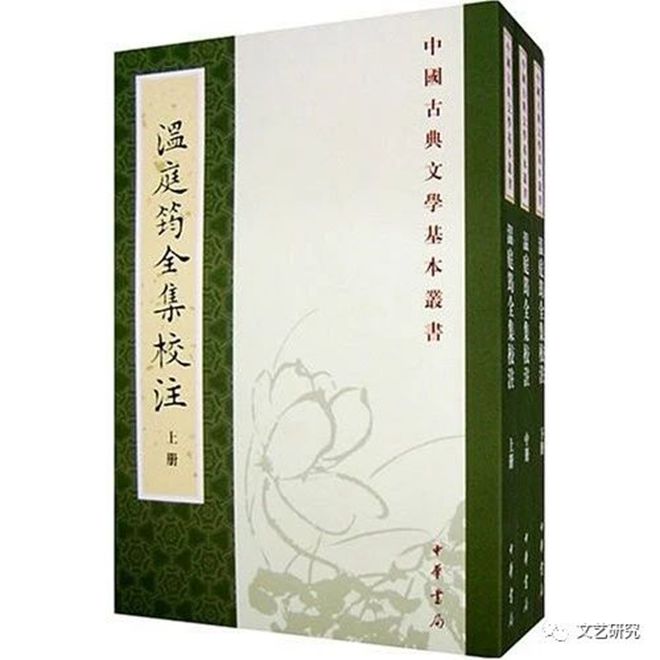
三、唐音清赏,文献大观
谢琰 您在整理、研究李商隐、温庭筠之余,又不断撰写或参与编写各种诗歌鉴赏书籍。据我所知,就有《唐诗鉴赏辞典》《唐代绝句赏析》及《续编》《唐诗名篇鉴赏》《古典文学名篇鉴赏》《历代叙事诗赏析》等多种。您对鉴赏的兴趣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刘学锴 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北大,文学史课着重讲“史”。代表性作品虽然选了不少,比如《诗经》选了几十首,但课堂上最多串讲五六首。不过林庚先生不一样,他讲课神采飞扬,擅长对作品的审美感悟和诗性发挥,有时一首诗能讲两个小时,我们听了很过瘾。这方面我受了一些熏陶,但学得不好,真正得他真传的应该是袁行霈先生。我总觉得,细读文本,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始终是研究的基础一步。我到安师大之后,这里的老师都是以讲作品为主,把“史”尽量压缩,因为培养对象是未来的中学老师。于是,对于名家名作的分析、鉴赏,就成为我日常教学与研究的一部分。
谢琰 最近几年,您仍笔耕不辍,发表了《读唐诗名篇零札》等札记,还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两巨册《唐诗选注评鉴》,您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大书?
刘学锴 这和我自己年轻时的教学感受有关。我从“文革”前开始接手唐宋文学课程。当时我就特别希望手边有一本像《唐诗选注评鉴》这样的书,除今人的注释外,把前人的注释、评论都搜集好,又有编撰者的疏解、评鉴作参考,那我讲课就方便多了。我做完温庭筠那三本书后,实在不想总跑图书馆去做新的课题,又不能忍受闲暇无事的状态,于是就写了这本书。开始时计划比较大,选了两千七百余首,基本把现存唐诗中的精品一网打尽,但精力实在不行,后来就压缩到六百多首。我觉得这本书对于中学语文老师和高校年轻教师可能有点儿用处。我对这本书的定位,就是切实有用。现在有些新的文本细读方法,我不会。我完全是采用传统方法。而且我一般不大讲“诗法”。诗法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若没有诗性诗情,光按诗法写诗,写不出好诗。我讲诗,就是一边解释,一边鉴赏,能够把诗歌意境传达出一二,就满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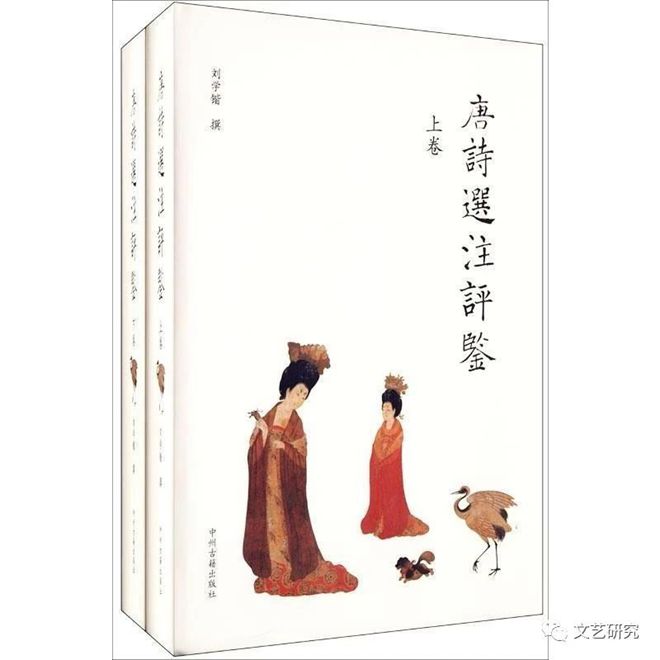
谢琰 您的名字总是和余恕诚先生联系在一起。1997年,您在《唐诗风貌》的序言中说:“这纯粹是一种纪念、一种对我们之间三十余年共事相知情谊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2014年,余先生去世了。您可不可以谈谈您和余先生合作研究的经历?
刘学锴 恕诚去世后,北大出版社出了三本纪念文集。其中《余霞成绮》这本书里,除我的《悼恕诚》外,还收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和恕诚合作撰著有关李商隐的几部书稿的具体情况》,里面说得很详细,这是一种交代。
谢琰 您曾谦虚地说:“我不敢自诩为恕诚学术上的真知音。”可在旁观者看来,只有您的学问以及您和余先生的情谊,才配得上“知音”二字。我想请您谈谈,余先生治学具有怎样的特点和魅力?
刘学锴 恕诚这个人,人如其名,既恕且诚。他擅长理论研究。他为人很谦虚,但实际上对自己要求很高。他私下里跟我说过,无论做什么都要与众不同。他的论著里,我最喜欢的是《唐诗风貌》。这本书里的文章,都是在切实感受基础上写的,文字也很漂亮,尤其是前两章。我和他不大一样,我比较侧重于融通,没有他那样事事追求独创的精神。但我们合作研究李商隐,基本上没有任何障碍。最能体现我们两人的合作精神的,应该是增订重排本《李商隐诗选》。当时《集解》已经完成交稿了,在此基础上修订这本诗选,与初版大不相同。《前言》中关于李商隐艺术特点的那部分,我让恕诚来写。他提出了“以心象熔铸物象”的观点。过去很多人都提过“心象”,提过“物象”和心物关系,但“以心象熔铸物象”的提法,过去没有。我也不是特别懂,但我知道这是他的独得之见。对于李商隐一些具体作品的解读,我们有时也有不同看法,一般都彼此尊重。《李商隐诗歌集解》的第一稿是由我完成的,然后由他用铅笔在上面做修整、增删。抄改的时候,他抄改了一部分。其中有些篇章,我把握不定,就会询问他的意见。比如《辛未七夕》,过去张采田认为是为令狐绹而作,我不同意。我主张义山妻子王氏在大中五年春夏之间就去世了。恕诚就此提出一种说法:这是因为自己妻子逝世,于是连牛女一年一度的相遇都很羡慕。我觉得很有道理,就连带着将其他两首关于七夕的诗也照此处理。还有一些诗,我们会有分歧。比如《夕阳楼》,恕诚比较赞同纪昀的看法,认为此诗“不免有做作态”。最初的稿子就依循这个观点,说伤了“浑朴之气”。后来做增订重排本,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绝句,就是讲韵味的,不能用古诗标准来要求它。甚至五绝都可以直白点,但七绝必须讲韵味、风神。所以我又将观点改过来了。总的来讲,我对他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很佩服的。他的三部书,我觉得最能传世的还是《唐诗风貌》。他有时一年就写一篇论文。他编写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文学史教材的晚唐几章,也特别认真,全力投入。这点我自愧不如。还有他上课,投入更多,讲得太好,我没法跟他比。
谢琰 除了余先生,您和傅璇琮、陶敏、陈铁民等先生也有学术交往。您和这几位先生,都对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谈谈您与他们的交流与合作吗?
刘学锴 他们三位,我都很佩服。三位总的特点,都是偏重考证。傅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军人物。他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唐代诗人丛考》,是开风气的,走的是文史结合、偏重考证的路子。他花费很多精力主编大型书籍和参加公共事务,还是我们学校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对文化建设贡献很大。陶敏先生我非常佩服。我最初接触他,是1990年在西安开会讨论重编《全唐五代诗》。他的考证非常细致、扎实,《全唐诗人名考证》真是下足了工夫,很难挑出大的毛病来。他应该是我们这代人里面做唐代文学考证最有成绩的人,而且为人极好。说句不恰当的评价,他是“高级义务打工者”。他帮助别人做研究,不计较任何回报。比如岑仲勉先生校记的《元和姓纂》,郁贤皓先生请陶先生帮忙整理,他就投入很大精力。我们做《增订注释全唐诗》,陈贻焮先生让我和余恕诚主编第三卷。我们对人名考证远不如他熟悉,我就力邀他参加。他一口答应,甚至还说:“我到你那去吧,我把资料都带过来。”我说:“还是我把审订稿寄给你吧,你增改了直接送陈铁民就行。”所以第三卷里包含了很多他的考证成果。陈铁民先生也是偏重考证,主攻盛唐名家,成绩斐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代文学史》,他是主编和主力。他的《唐代文史研究丛稿》里有一篇十来万字的大文章《唐代守选制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很见功力。最近我们一起做《增订注释全唐诗》的修订,他是总主编。原定的十个主编,白维国、彭庆生、余恕诚、陶敏四个已经去世了。现在统稿、审定都靠他一个人。我听他说,有位日本学者曾称赞《增订注释全唐诗》功德无量,他这才起意重新修订《增订注释全唐诗》,把近十几年的成果都尽量吸收进来。
谢琰 期待这部大书早日问世!和您聊了这么久,我从中获益很多,相信广大读者也能得到启迪。最后,您可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治学经验吗?
刘学锴 谈不上经验,只能算个人的感受。说三点吧。第一,笨人用笨工夫,也可以做一些有用的工作。第二,前人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的研究对象,后人照样可以做出成绩,起码可以添砖加瓦、拾遗补阙。第三,如果自知才学、识见和时间都有限,与其蜻蜓点水,到处都沾一点,不如集中力量攻其一点。当然,是有价值的一点,而不是被历史早已淘汰的东西。若有余力,再旁及其余。
我自知先天不足,悟性不高,缺乏才气、识见,后天又学养不足,短板甚多。如果说我的某种成果可以传世,那是鼓励,是不实之誉。如果说我的整理和研究多少推动了文学史相关章节的改写,也许还差不多。任继愈先生谦称自己是过渡的一代,我只能是过渡的一代中最平凡但多少做了些实事的人。
谢琰 您太谦虚了!作为后学晚辈,阅读您的著作,学习您的治学方法,体会您的人生态度,是激励,也是享受。再次感谢您!
刘学锴 不是故作谦虚,是实事求是。谢谢你!
(责任编辑 守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