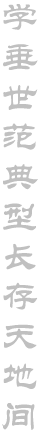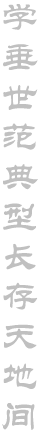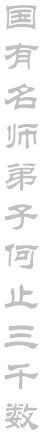怀念余恕诚老师
方锡球
余恕诚老师生病,我知道得较晚。6月11日,是我最后一次去北京探望先生。我带着女儿,余老师送我到楼下,我走了好远了,我女儿回头说余爷爷还在院子大门口目送我们,这是他生前我见到的最后一面。得知他病危的消息,我安排好工作,匆匆赶往北京,先生却在我到达之前一刻钟与世长辞,我心里很痛,这是我的终身遗憾。之前我自信,我赶不到,他老人家不会离开;同时,我又自责,我不应该这样慢,应该像大芹书记那样,一下车直奔医院,若那样,我是可以在两点一刻到达医院的。
先生给我的心灵感动太多。我与先生相识的时候,读本科二年级;到三年级时,先生给我们讲唐诗研究。他的学问是深入人心的文化关怀,他的悲天悯人之心让我终身难忘,课堂上的儒雅风范至今如在眼前。2005年,我大学毕业整整20年,重回母校,忝列先生门墙,攻读博士学位。我还记得入学考试的考场上,先生坐在我身旁良久才离开的情景,之后对旁人说,“看着他和年轻人一起考试,我只想掉泪”。还记得,第一次博士生开会,弟子侍坐,先生向同门介绍我,以“老师”相称;还记得,他在古稀之年咨询建设博士后流动站时的艰辛与疲倦;还记得,他为了学科发展,花了自己的钱;还记得,70多岁的先生出差开会,带着干粮来回乘公交;还记得,我人生遭遇坎坷,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爱!
最难忘的是我读博时,冬天,他每周到我冷寂的宿舍,一去就是半天,嘘寒问暖,传道解惑。若是天气好,我每周1~2次陪先生散步,讨论问题,接受指点,有时也在山路旁的椅子上坐坐。赭山的路上留下我们师生无数脚印,先生留下的是无私和慷慨,留给我的是难忘的坐在春风中的愉快。每当我有体会或遇到思考的困惑,我都要找到先生,请教一番,讨论一番。在讨论中,我们又不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想法。虽然这些问题和想法一时没有办法解决,但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将是很充实的了。
先生对我既关怀又严格。我们学生都把余老师当做是慈祥、温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就将师大当做我们温馨的家。记得大二那年冬天,在西大门遇见他,他问我《唐诗选》看了多少,要求读大家文本;临别时,见我衣着单薄,就说要是不讲究好看,他还有棉鞋、棉裤,可以拿来穿。但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先生和我的谈话,往往于宽容与蔼然间,蕴含着不能动摇的原则;在娓娓的含蓄话语之外有严格的要求。我读博士学位时,开学第一天,他来到我的宿舍,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回到母校,做个学生,不搞特殊化”。傅璇琮先生来芜湖,当时我在安庆,他用电话催促我回到芜湖,接受傅先生的指点。可能是我的节奏慢了,等我到芜湖时,虽然向傅先生认真请教了,而隔天,他让秘书通知所有博士生必须去听傅先生的讲座。讲座开始,先生用半小时讲20世纪80年代学术史,以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为例,讲述今天唐诗学术的繁荣,与两位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和颜悦色、和风细雨中,他对学者和学术的敬畏,包含着不能动摇的威严,这在我,的确属于迟到了二十年的春风化雨。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他几乎三管齐下:聘请权威学者开题;他对自己把握不准的地方,向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的专家咨询;申报国家项目,检验选题价值。
32年来,我的成长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深情。
我的先生一直默默支持我所在文学院的发展。介绍专家学者支持我们,指导我们申报硕士点、建设重点学科,为我们培养青年教师。先生去北京治病前,还一直担心我校一位青年教师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可借助的平台。他的人格精神熏陶的不仅仅是一届届门人,不仅仅是安徽师大的学子,同时也感染了国内许多后起之秀。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许多人纷纷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表达沉痛的哀悼之情。
往年这个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期间,我一般要到先生家走走,聆听他亲切的教诲;今年的中秋节与教师节,我们却只能在这样的一个会上追思我的恩师。“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先生离去的这些日子里,我总感“秋霖腹疾”,始终无法平息这“荷叶枯时”的秋恨。这种遥遥无期的缅怀和“碧海青天”般的思念,将成为我们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早上,我再次走进先生的讲堂、走进先生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再一次走过先生走过的路,还是那么熟悉,“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在新学期,在早晨母校的校园里,我是多么渴望再见到先生那蔼然的面容和那父亲般的背影。
我深知,最能慰藉先生的是我们,相信所有先生的弟子,会用踏实而真实的一生,让他老人家走得放心!
(原载《新安晚报》2014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