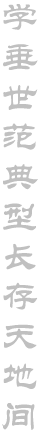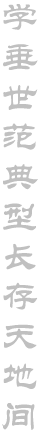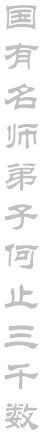余恕诚老师琐忆
俞晓红
1978年秋天,我从中学直接考进安徽师大中文系,成了“七八级”的一员。当时的系主任是知名学者、“龙(《文心雕龙》)学家”祖保泉教授,也是我们的授业老师。我们和1978年春天入学的七七级,入学相差仅半年,两届间有很多人彼此熟悉来往。听到七七级同学称,余恕诚老师课讲得很精彩。于是,没有课时,偶尔会有三五个同学从三楼上到四楼,溜进七七级的教室去蹭课。
硕士毕业时,我留校任教,有幸与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诸位前辈近距离接触,知道刘学锴、余恕诚两位老师并称“刘余”。那时每周一次教研室学习活动,因此能够经常和“刘余”睹面。那些年,我常去老教师的课堂观摩,因而也听到了“刘余”的课。课堂上,刘老师是三严:教风严谨,教态严肃,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余老师是三温:态度温和,言辞温软,情感温馨。慢慢地,也就知道了“刘余”一词的内涵。同事间或朋友间在学术上合作的有不少,像“刘余”这样能够携手合作数十年而无有芥蒂的并不多。
祖先生非常重视学生国学功底的培养,曾设想从中学、甚至小学或幼儿园起,就开始办国学班,实行一贯制,然后直升到师大中文系,藉此培养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高级人才,甚或能出几个国学大师。余恕诚老师则秉承了这一教育理念,并准备付诸实施。为此,余老师来找我,娓娓而谈,谈“国学梦”、“大师梦”,谈梦的内容、目标和实施计划,谈课程体系、师资选择、教材编撰,问我愿意不愿意做助手,帮他实施这个计划。我当即表态说愿意,余老师便让我先做方案。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谢昭新教授也非常支持此事,乐意为国学班的开办提供条件。中文系的一位老教师,还给时任南京师大教科所所长、教科院院长的校友朱小蔓教授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办国学班的重要价值,朱小蔓遂转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先生那里,由赵朴初和其他几位政协委员写成提案递交“两会”,以期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我的大学同学宋中华闻讯后,在淮南搜集了全套的中学语文教材和教辅材料寄给我。两周后,我把方案拿给余老师看,他非常满意,带着我一起去附中、附小调研。附中的宛炳生校长是著名词学家宛敏灏先生的公子,而宛敏灏先生作为中文系的前辈学者,与余老师兼有师生之谊、同事之情,因此宛校长要比常人更多地懂得办国学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对余老师的设计颇为赞许,为此专门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将附中语文教研组的骨干教师全都请到,一起倾听余老师的梦想,并对办班方案进行论证。会后,宛校长还组织了几个老师,就方案实施进行了成本测算,并对国学班的生源及学生的出路保障做了深入的思考和研讨。此事前后经历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由于在争取上级主管部门高考录取的政策支持和办班项目的经费投入时,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一梦想悄悄流宕了。今天看来,这一设想颇具前瞻性眼光,其意义也十分显明,然而在20年前,却宛如民间流走的一个传说,半空游动的一片云霞,悄然来去,未留声影。
我读博时,从我就读的硕士生李小荣恰好与我同期。2004年春夏之际,她的学位论文写到紧张处,也是我的学位论文即将杀青之时。5月29日那天,我在上海师大的宿舍,忽然接到余老师的电话,说他的硕士生论文答辩已安排在6月5日,问我:“你愿意不愿意让李小荣和我的学生一起答辩?”我大为感动,连声答应。谁都知道,硕士生单独一人答辩,所有程序一个不能少,答辩成本相对很高,经费却极其有限。答辩能够“搭便车”,等于省去了我作为硕士生导师应做的所有工作,而且大大降低了经费与时间成本。在我没能从容考虑此事之时,余老师主动打长途电话关心我,不让将于6月2日答辩的我分心,安排得如此妥帖,却用商量的语气,这一切,怎能不让我感动呢?
博士毕业回芜了,9月的一天,我在西大门内偶遇余老师。余老师微笑问我:“你回来了?读博辛苦不辛苦?身体还好吗?”我说,身体还好,因为每周至少三次跳操;读书成了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不觉得苦。余老师看看我的头,又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有白头发了。是啊,我说,最后做论文阶段,关门闭窗,仿佛置身空谷,声色不闻,凝神定气、思接千载之际,能听见头发一根根变白时发出的“咝咝”作响声,从根部漫到发梢。余老师笑了起来。我问余老师近来做什么,答曰在给本科生上课,每次有课的前一天晚上,要重新备课,会晚点休息。“每一课都要重备?”他微微笑道:“是的。”我从内心感到震撼。随后不久,我将读博前使用过几轮的手写教案——一摞子硬面抄,扔进了纸箱,搁在架空层储藏室,然后从头开始备课,撰写电子教案。从此以后,我每给一个新的年级授课时,就会重新搜检学术界新说,不断更新我的教案和课件,形成了新的习惯。一晃10年,算起来,余老师那年业已65岁了。
也是那一年的冬天,我的一本小书《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笺说》在中华书局出版。我拿到了20本样书,先到院里,放进几位老师的信箱。没几天,我在老语言所楼外的转弯处遇见余老师。余老师随即停步,说已拿到了书,从头到尾读过了,谢谢。我有点不安、带点期待,问余老师:“如何?”余老师仍是微微含着笑,温和地、也十分清晰地说了四个字:“传世之作。”我大感惶惑和惊讶,问“会吗”,余老师极为认真地看着我说:“以后别人要研究王国维,是绕不过去你这本书的。”当时我的反应大概比较憨,什么也没说,笑着离开了。想起来,大约我那时是不信的,以为不过是余老师的鼓励提携之词,要安慰一下鬓已见白的我而已。
又年余,我的博士论文几度修改后,将要付梓。余老师闻讯,特地打电话给我,说,晓红,你不要先急着出,你这个题目很好,磨一磨,等一等,多思考,多积累,可以承担一个大项目,再出成果。我说:余老师,我回来这两年,一直在修改;如果不出,时间长了会有被盗用的危险。余老师说,别人也看不到啊。我说出了我的担心:我论文一年前就上了知网博硕论文库,当时缺乏安全意识,既没删除注释,也没申请加密,现在我已读到几篇疑似抄袭的论文了……“啊?这样啊?”余老师有点震惊,没再说什么。现在想想,余老师话里有太多的关心和建议,我当时怎么就没明白呢?
2010年7月24日,在杨屹、王大明、许北雄、魏民、姜立安(安妮)、孙海珍、王秀琴、任良韵的长期酝酿和积极推动下,安徽省朗诵艺术学会在合肥成立。学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经典诵读进校园”。会长杨屹、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大明、副秘书长姜世平,既是主要发起人,又都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所以“经典诵读进校园”的第一站,自然而然就到了安徽师大。选择朗诵作品过程中,我发现书店里提供给中小学生诵读的经典诗歌选本较多,而供在校大学生诵读的经典诗集一本也无。站在合肥书店里翻阅的我,当即萌生了要编撰一种适合中文专业以外大学生阅读的经典诵读选本的念头。回来后,我在电话里将这个想法和余老师说了,余老师竟是十分赞同。我请余老师担任审稿,他欣然应允。他还建议将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比例确定为65:35。彼时担任学校出版社总编的汪鹏生亦是我大学同学,一闻此讯,深表支持,立即列入出版计划。由于体例上“延伸阅读”的需要,题名虽为《大学生必读的中华经典诗歌100首》,涉及的诗作却有200余首。古代诗歌的篇目比较容易确定,现代及外国经典诗作的选目,是在同事杨四平、张应中两位老师襄助下完成的。我撰拟了编写纲要,包括读者定位、编写目的、原则、体例和诗作文本,打印了一份,送到余老师家中,请他过目。没想到第二天,余老师就回我电话,对富有创意的体例和选目表示首肯。三个月后,书稿撰成。11月20日,我将书稿打印出来,送到余老师家中,请他审订。本来20多万字的书稿,浏览一遍就要花很多的功夫,我请余老师慢慢看,“两周三周都可以”。然而余老师却不肯稍有停歇,居然两天就看完了所有内容,第三天上午就打电话给我,“你现在就来取”,他说。那天是22号,临近中午,淮海村一片秋阳普照,暖暖的,我刚走上山坡,远远地就看见了余老师,正读二年级的博士生王树森右手搀着他的左手臂,左手抱着牛皮纸袋,两人靠得很近,慢悠悠地向外走来。我急忙小跑迎上前去,说余老师您怎么不在家等我,就送出来了?余老师仍是淡淡的笑容,说:我也正好要去开信箱,走走,顺便。他在路边站下,树森递上牛皮纸袋,余老师拿出书稿,一边翻看,一边告诉我需要修改或润饰之处。有一首写女大学生宿舍的诗,余老师觉得写得倒是蛮好的,但进入“经典诵读”选本供在校大学生使用,恐怕有点不合适;又说,高适的“适”字,应写成繁体的“適”字;目录中词作的篇名,建议参考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的形式,用词牌加括号首句的方式等等。书稿上,余老师用铅笔写的字、做的记号,迹淡形小,随处可见。又感慨于经典的难以普及,由侃侃而娓娓,我感动之余,“谢”字而外,惟有聆听而已。好半天了,余老师意犹未尽,说送送我,我坚辞,但他仍与树森一起又和我走了一程,树森在左,我在右,快到西小门了才罢。
2011年3月的一个晚上,余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有个课题《皖南诗歌史研究》,已有几个硕士生、博士生分段选了题,如朱少山写了《北宋皖南诗歌研究》。他轻声款言:“前面时间段都好安排,你能不能和元明清其他几位老师商议一下,看看硕士生中有没有文笔好的、功底不错的,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三个人,每人分一段写?也不急着选,慢慢考察,确实能做这个题目的,再让他做。”尽管余老师用了商量的口气,殊不知这也是一项任务呢。我当即答应,随后就和同段的老师商议。由于在读硕士均已有了题目,更换不便;等下半年入学的新生,又要有个了解的过程;等了解了又觉得未必合适……如此这般,又是一年过去,尚未确定。每与余老师谈及,余老师说,不急,慢慢找。终而选了从我就读的硕士生赵越,和她详谈了课题要求,赵越十分乐意做,遂以“清代皖南诗歌史研究”作为学位论题。动笔之前,赵越就在电话里接受了余老师的指导;待开题报告写出后,打印了送给余老师看,余老师次日即打电话给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要尽量选本地诗人写皖南风貌人情的诗作来分析,突出皖南特色;二是要增加外地诗人写皖南的诗作分析。说起来,余老师竟是指导了赵越论文主体框架的撰写。遗憾的是,在赵越将论文定稿送到余老师信箱里时,余老师病倒了,去了北京,我和赵越再也没有了受教的机会!
2012年3月20日,汪裕雄老师因病谢世了。黄昏时分,外子在家中接到了余老师的电话。余老师说,绪左,你和晓红两个人都很有才华,我听说学校有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去世,都是你们撰写的挽联;平时有什么事,我不敢烦扰你们,现在汪老师走了,汪老师是个好人,人品高尚,学术造诣高,你们俩能不能琢磨一下,写个挽联,能够概括汪老师的主要特点的?余老师这个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我下课回来,听说后十分感动。汪老师是徽州绩溪人,为人温儒裕和,行文雄古神秀,当得“裕雄”二字。他给学界留下的精神痕迹,是《意象探源》、《审美意象论》、《艺境无涯》等著述。次日临近中午,挽联终于拟好:“江畔滋兰,生而有道,慨德性裕和,秾李夭桃齐俯首;易中源象,境亦无涯,惊徽风雄拓,典型文望须留传。”遂打印了两份,一份送给余老师寓目,一份按余老师嘱咐,送给陈文忠老师斟酌。到了陈老师家,方知还有其他几位老师也撰拟了挽联,一并都送在陈老师家。选定之后,余老师又电话来嘱咐说,绪左,你字写得好,你把挽联写出来挂。也许是2000年周勋初先生来主持袁晓薇的答辩时,海报是绪左毛笔书写的缘故,余老师的印象特深,遂执意要绪左书写出来。那时已是晚上,要准备纸笔、还要去挂,来不及,终于作罢。我体会这意思,余老师是觉得,要学生亲自撰拟、亲手书写,才能够表达大家对汪老师逝去的深深哀恸之情吧?
那年7月,余老师听说我将去皖江学院工作,对向他征询意见的校领导说,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晓红教授很适合做行政管理,她很能干。而我那一去,事务太多,工作太忙,竟然很少再见到余老师,有时候连通个电话都不能。2014年4月,听说了余老师染病去北京治疗的讯息,我很伤感,觉得他是太累了。遂与马三保书记说及此事,马书记说,我们一定要找个时间,一起去北京看望余老师!然而这个约定却因现实种种缘由,没有来得及实现。暑期我去了美国学习,余本玉告知我余老师病逝的消息时,正值我回国的前一天,旋悟这已成终身遗憾!
刘学锴老师也许是最了解余老师的人。他觉得,余老师是“太累了”,“正是由于这种重生命的密度甚于生命长度的人生信条和对自己近乎严苛的要求,过多地透支了他的健康,使他在还能做出更多成绩的年岁,离我们而去,留下无尽遗憾”。汪裕雄老师去世时,我曾写了篇题为《生命留给世界的痕迹》的博文,其中有云:“常言人生是过程,我们在过程中获得意义。无论是长是短,给世界留下点精神痕迹,已了不起了。”余老师的著述,也是为我们这个世界留下的辉煌印迹啊!
现在体会,很多事情真的是要自己经历过、体验过,才会那般地刻骨铭心。为何我每在回想往事时,会浮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自责和憾恨呢?还是说,作为老师,时时刻刻、无私无怨地提携关照学生,帮助青年教师成长,已经成为前辈学者自觉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了?或者,究其本质,原是我们师大中文系80余年的老传统呢?汪老师也好,余老师也罢,他们不经意间的一举一动,一句话,一篇文,如此这般,如彼那般,潜移默化之际,浸润了后辈学子的灵魂。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于江城
(作者简介:俞晓红,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文于2015年2月5日《大江晚报》,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