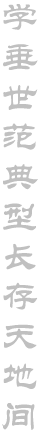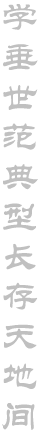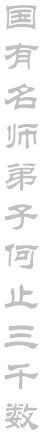关于余恕诚老师在学术和教学上的卓越成就,在座各位、特别是留在母校工作丁放、传志,比我更有发言权。作为宛老、刘、余老师首批指导的唐宋文学研究生,几十年来一直受知于刘、余老师。所以传志令我发言,我亦不能推辞。我只谈几点个人的认识,谈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唐诗学研究
余恕诚老师不但是唐诗学家,而且可能是继闻一多、林庚之后,最重要的唐诗学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余先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向对唐诗风貌及其成因的潜心研究,有计划地撰写了十多篇很有份量和创见的系列论文,其中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就有六篇。其专著有《唐诗风貌》(《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诗家三李论集》等。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如高层政治生活对李杜创作的影响(这一点他得益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而且他和刘学锴先生对此书的价值有迥异时人的非常一致的看法);如王昌龄、李白等人以一般征人口吻写作的边塞诗,与高岑等军幕文士以自我抒怀为主的边塞诗的异同;如论唐诗对时代反映的深度、广度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美,特别注重对有唐一代士人的精神风貌、胸襟气质;而对唐诗的整体刚健物质作追本溯源之论,又特别注目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这一漫长的民族大融合过程所带来的胡汉诸民族精神文化的摩荡和融合及雄强之气的注入,从而对唐诗阳刚之美在气象、内质、情态方面的突出表现作出有力的说明。(以上表述采自刘学锴先生为《唐诗风貌》一书所作的序言。)
二、李商隐研究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余恕诚老师与刘学锴先生携手合作,致力于李商隐研究。先后出版了《李商隐诗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初版,1986年增订再版)、《李商隐》(中华书局1980年)、《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等专著;还发表了《李商隐的无题诗》、《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证》、《李商隐生平若干事迹考辨》、《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等一系列单篇论文。
李义山诗风与李白、杜甫不同,多用比兴象征,隐晦朦胧,意蕴深曲。刘、余先生审度对象的特殊情况,认为与其勉强撰写以著者已意为主的新注,不如集思广益,以集解新笺的方式来整理研究,较为实用。无论编著诗选或集解,都注重实证,避免臆测;同时注意在社会、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寻求中介,并结合运用心理学、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避免把李诗本事化、标签化。文革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义山诗成为唐诗研究热门,从者蜂起。而如刘、余先生这样积十数年之心力,孜孜矻矻,由诗选——评传——集解,滚雪球般地壮大成果,为义山诗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者,在学界罕有其匹。
《李商隐诗选》(刘、余先生合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这本《诗选》选目精而分量适当,注解详博(释词、笺事、阐意、谈艺兼营),资料翔实,前言扎实而附录有用,能作深入研讨诗人生平和全部作品之导引,在丛书中水平及层次均属上乘。而《李商隐诗歌集解》共五分册百余万言,是李诗的会校会注会评会笺本。在冯浩《玉溪生集笺注》后,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经过全面整理、资料丰富、使用方便的新校注本,成为对李商隐研究的一项持久的贡献。(后来,刘、余先生又编纂了《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上下册、《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全五册,皆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唐诗鉴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辞书出版社率先出版《唐诗鉴赏辞典》,在全国出现了长达近二十年的鉴赏类书出版热。而《唐诗鉴赏辞典》迄今印行几三百万册,创造了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而这部辞书也获得了国家图书一等奖。而这部书的大量的赏析文章,出自于刘、余老师为首的安徽师大写作团队。其中刘老师撰写达八十余篇,余老师撰写七十余篇,作为他们首届研究生,刚毕业的本人撰写一百二十余篇。此外赵其钧也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辞条。宛老(敏灏)年事已高,也象征性地写了几篇。总共要占去全书百分之三十的篇幅。如果说当代唐诗研究有一个鉴赏学派的话,中心就在安徽师大,领头的就是刘余老师。我在校念书时,他们就曾经教导我说,说不要鄙薄此道,远不所有的专家学者都长于此道。如果没有刘、余老师的教导,就不会有《诗词赏析七讲》《诗词创作十谈》《周啸天谈艺录》等著作的出版。
四、培养人才
在这个方面,丁放、胡传志比我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我只谈谈毕业之后,余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毕业后,刘、余老师和我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母校成立了以余老师为主任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后,2003年中心以刘学锴先生的名义申报了一项《诗情画意的安徽》的项目,余老师电话约我回母校做这个项目,主要是构思框架和拍摄图片。出版社的人告诉我,余老师说用我可以一以当十,这个话有点近乎偏爱了。做这件事,我最为受益的是,弥补了在校攻读研究生期间除了芜湖,就没有去过安徽别的旅游景点之遗憾。同时还写下了《徽州民居》《太白醉月歙砚歌》等诗篇。而且就是在母校这个学术平台上,我认识并受知于王蒙先生。余老师在2015年的一封来信中写道:
诗集收到。昨天王蒙先生来师大作学术报告。今天中午我送王蒙由铁山宾馆出发去南京机场。啸龙赶来告别,把你的诗集递给我。这样,我们正好在车上欣赏你的大作。王蒙接连称赞:“写的真好”“写得太好了”!王蒙夫人也在旁边,她还记得你的《洗脚》《人妖》等篇。他们俩说当时就很欣赏。王蒙在车上朗诵了你的《洗脚》《人妖》《纽扣辞》等篇。说你的《人妖》是“仁者之诗”。“关心现实”“很幽默,又很雅”“写到这样真不容易”。问你在做什么?跟师大是什么关系?建议你寄上两本,一本给王蒙、崔瑞芳,一本给秘书彭世团。
不久以后,王蒙先生即有成都之行。他让彭秘书从网上查到我的电话号码,于是我们有第一次晤谈。那时他就主动地说要写一篇诗评。后来写了三篇。而同年,余老师在另一封信里说:
今晚在灯下,几乎把《欣托居歌诗》都读了一遍,真是一种享受。第一,我觉得这个集子已经不单薄了,印刷得又极好,足以传世;第二,既是道地的旧体诗词,又极富有时代感;第三,《欣托居歌诗》证明旧体诗词是有生命力的,今后还会有大放光芒的时候。
直到去年,余老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还和我有几次通信,他在一封信里谈到《邓稼先歌》:
《邓稼先歌》写得神完气足,读来感人,即使放在盛唐优秀诗篇中亦毫无逊色,获华夏诗词大奖是当之无愧的。我始终认为创作是第一位的,你走的路子是对的。
因为我是完全认同庄子“齐生死”的观念,从不承认“永别”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不认为余老师与我们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在与余老师最后的通信中,没有回避这个终极问题,我认为应该把“视死如归”,“置生死于度外”,“时刻准备着”这三句话作为座右铭,同时对人生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余老师回信说,他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
我愿重申这一态度,来纪念余恕诚老师。谢谢各位。